马上注册,参与互动,展示风采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立即注册

×
建筑风景画系列(1-4,未完)
夏日庭院
许多年前我在梦中随同一个人走在一条林荫道上,道旁有一辆小推车停靠着,车子上载满盆花,我们买下其中一钵,向一栋建筑样式陈旧的庭院小楼走去。
我在傍晚时分的院落驻足,微风从逐渐衰老的建筑拂过,绿色的草木从矮墙后姿态温柔地闪现,藤蔓植物在墙垣游走,视觉中有一种凉爽的感动。身边的人蹲下身,拿出诱饵呼唤草丛中的爱犬,夏日音符一般跳跃而出的金色小动物。随后,是大面积的静谧覆盖了那栋房屋和它的庭院。
它是怎样隐藏在城市巨大的喧嚣中的,并且躲过一次次或大或小的城市拆建改造工程?这于我是一个谜。我能解的是外墙遮盖下,那里并没有什么值得我期待的内容。然而我还是深深感到自己在异乡的孤独与单薄。我或许很想跟那个人谈谈房屋与家庭的话题,不过很快我发现这是个荒谬的念头,便放弃了。
我始终不曾走进那栋房屋。房屋的内容是不稳定的事件,偶然。而被街角三轮小推车、树木、藤条和花草围绕的建筑氛围,却如一幅印象派的画般会在记忆中闪现。我想想,自己与那座城相连的其实是一幅风景画,我在其中悬置过一条青春的裙子。青春没什么值得多说的,现在也没什么值得多说的,风景画中演变的脆弱人物都将被放逐他处。
无法终止的画卷,在向无法释怀的虚弱感表达致敬。
地下明室
老旧的地下室已经废除。蜜蜂曾在那儿筑巢,房屋的底层缝隙里还有干枯的断翅、残存的蜜吧?我靠在沙发上似睡非睡,一时想起,大笑不止,被自己的荒谬逗乐了。我已经不再手举烛火前往地下室,轻轻慢慢拾级下,如同静脉中的血液一样前往漆黑的地床。影子在墙面上跳动,摇摇晃晃,不知名的生灵蛰伏在那儿,我因此一次次陷入自己的幻想和异类生灵蛊惑的力量当中。工蜂也许还在室外的蓝天下画着一些奇异的不可思议的纵横交错的线路,不过总会回来的,地下室里有它们族群的雅典卫城。
绿色的地衣在墙上诞生并蔓延至我的手指,词语开始在我的指尖萌芽,喃喃作响。
我喜欢房屋有一层没用的地下室。
您真让我惊讶。
来传递改造屋舍福音的使者笑了。但街道办的事琐碎繁多,他懒得与我在这个问题上多纠结。
很快大家推倒了笨重的隔墙,邻里几家沟通成一室,希望把某种价值从无用的黑暗中找回光亮,放大尺寸。随后用白灰、瓷砖、大理石以及灯光、落地窗来装点它,照亮它。摸摸新墙面,美妙的光滑度,光从落地窗倾洒,这样的慷慨。好大一间地下明室。
我内里的光也被这样倾洒出去。
“为什么不赌一把呢?”说这话的人租下了这片地下室,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一些员工,和许许多多的帽子、丝巾、瓷器、茶具、俄罗斯套娃……它们已经在长方形、梯形、圆柱形各个陈列柜上拥有了自己的商品生活。这是奇妙的,当年轻女员工伸出手指熟练旋转一顶宽边软帽,或是抽出一条丝绸方巾向顾客展示物品的美丽之时,我看着很快乐,轻盈的、舞蹈般的,缓缓衍生的纯粹感官的逸乐盛宴。包括女员工白而细的手指,以及指甲盖上月牙形的珠光染色。
地下室已经在五彩斑斓中漂浮起来。建筑四周深色的泥土渐渐坍陷,房屋的根基薄而透明。
房屋的工程从来就没能完成。
阳台鸟窝
黑暗在房间里静默涌流,温柔的喑哑如此美好。
醒来的人心有不甘,但还是披衣下地,开始在一团漆黑但有着坚硬家具和柔软物件的房间里摸索着走动。房屋的另一侧,那里有一个小小的露天阳台。阳台里有一只鸟窝型的藤条吊篮,不过看上去很像一件陈旧遗物。我用手轻轻触碰了一下这只空藤篮,它便在露台朦胧的月色中懒洋洋地,毫无目的地原地兜着圈子,一圈,一圈。
她常常会坐在这只藤篮里。她似乎有轻微的病症,偶尔会有外出弹拨吟唱的演出活动,不过更多时候,她的生活就像一幅画一般空闲,脱离现实。 “哦,我唱鸟语。”她说这话时就躺在这只吊篮上,羞怯地笑,同时将脸埋进褐色卷发,就像树林里裹着深色头巾的鸟儿在啾啾——我因此知道她有一个鸟的梦。
“为什么不多出去走走呢?真正的街道、人群、美食、声音,还有运气……”
“或许这些也只是人们自身的摆荡,我在这里摆荡也可以的。”她抱歉且伤感地说。
我将手肘支在阳台扶手上,就那样看着她,我不会帮助她,也不会反驳她。她也只需要我用目光陪着,在 她身边站站,或者来来回回走动,供以一点生命的气息。
藤篮一圈一圈荡着,无法停止。我看见她灰蓝色的裙摆滑下来,在夜风中微微摆动。或许这只逐渐破旧的藤篮也在抓伤她,但她表情温和,始终不曾喊疼——她内心里是否有某种绵密且轻柔的熨压、忍耐?然而我没有问过她,我不应该出于自己的好奇而迫使这份痛苦开口诉说。时间缓缓地深陷入她的眼眶、肩胛骨,她的存在终于开始变得越来越可疑,如同一片灰蓝色的鸟羽,有一天她从藤篮上消失,不曾再出现过。
我又推了一下藤篮。它不能这么空空地看着我,令我疑惑,令我难过。
应该撤走它?或许也可以重新填满它?我沿着藤篮走了一圈,轻轻爬进去,同时我用双手将薄毯拉到下巴处,如一只甲虫蜷缩在网兜里。“哦,我说虫语。”我愉快笑起来,一时间忘了自己是一只陷进现代笼子的猩猩。
阳台上已经洒下清晨第一缕光。外面的世界,真实的生活,随后会到。
无名的房间
我的行李很轻。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不必过于看重自己的人生痕迹,以为自己每一块碎片有多少价值吧?我还没老去,我的手曲伸自如,活动十指我就可以在空气中灵活弹拨,但我清楚地知道,它握不住东西。我确实失落了很多东西,剩下的也随时可能悄然滑落而不为我所知。
我在这间看起来似乎延伸到很远处的无名房间里,无所事事。这世间所有的房屋大概也都是某种隐喻模型吧?对一些人来说是停泊的游轮,对另一些人来说可能是一艘欲前往彼岸的移民船。我没有什么着急的,平躺下自己,等待。毕加索正在为《晨歌》中被打碎的女体伸出援手,他帮助碎片们坚持,保持住隆起与凹陷的曲线,耐心在房间等待。
我会成粉末,尘埃。死亡在这间房里将抵达一个人最深的渴望。
但是毕加索笔下的生命激动人心。碎片里藏匿着弱小的胸腔,它们也许会奇迹般拼凑自己,曼妙女体将站起来走出房间?那把讽刺性的曼陀铃或许并不甘心从此弦断喑哑。
刚刚服务员来过了,她三两下就把房间清扫干净。服务员一般都是轻悄悄地存在这栋楼房的某一个角落,懂得怎样使自己被遗忘。她的话也总是简单而令人愉悦:您的床单需要换吗?还有什么需要的?我可以给您拿来。我惊讶她的工作——走过哪里便会轻松抹去那里的痕迹,让那里的物品快速恢复秩序和清洁。她是怎样做到对那些曾经栖居房间的灵魂的寄语充耳不闻,把碎片、灰尘,统统清扫出去,或把床铺罩起来的呢?这里,那里,每一间房或许都是一张欲望无尽的脸?每一张脸都干净得有问题。
尘埃、碎片在我的身体里吱吱响,发出低声轻唤。我在这间一尘不染的房间里陷进被自己激发起来的眩晕之中。
去那里吧。那里,你的眼睛会看见树林和星星。
有人坐在窗沿的靠椅上,指间闪烁着烟蒂的火星。他在看着我。他穿着一件深灰色衣服,口袋很多,像一格一格抽屉,这让他看上去像一只沉重的箱子。然而他眼神和善,哦,一个善良而背负了太多抽屉的人。他显然不是毕加索,但他似乎同样思考着如何行动,阻止我的碎片一块块自行滑落。
有个圣人的影子治愈了街角一个瘸子。用影子治愈病人的圣彼得。我笑起来了。
死亡是最后的领地,不用急着去——你还有梦想的自由。他吸完了那支烟,伸出手覆盖住我的手。手暖而宽,指缝送出烟一般的线路图。我循着着这烟看去,是他祝福与我的一片林木和星星。
将我带到这里的死亡的力量,慢慢消失。虚掩着的窗户,略微吸纳着外部世界的空气。
几年后的一天,我在一棵树下描绘光影,我听见脚底下的窸窣声,我的影子奇异地从我脚边略略起身。我想画下她,我知道画阴影不能乱涂,要落笔轻抬笔重,投影的边缘要轻轻地勾画,一条线在另一条线旁边,再一条线,一条线。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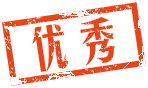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经典文学网
( 苏ICP备19050466号-1 )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经典文学网
( 苏ICP备19050466号-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