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锡民
偶然读到峡谷幽兰写的诗歌《我喜欢的树》,竟连续读了两遍。
“我喜欢的树/在光线下卷曲/在暗里,劲拔/或制造吸力”……
生活中的树有诸多的实用功能,与油盐酱醋茶对应的是桌椅板凳床,诗人在这里变一般意义上的实用为背靠大树好乘凉的“诗用”,且有新意上的“点突破“。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是树荫的因素,人们不说背靠电线杆子乘凉,不说背靠一根筷子或一根筋乘凉,原因就在这里。进一步的追问是,卷曲意味着遮荫能力的减弱,难道诗人喜欢的是一棵漏光的树吗?诗人没有给出答案,与此同时,诗人却毫不含糊地亮出自己的观点,即“乘凉,不应是寄生性的”,这样的观点不能说是对傍权力或傍大款式的乘凉的批判,但至少是一种抵触,一种对传统乘凉话语语义裹挟的挣脱。诗人明确地表露,她心目中的树是一棵具有鲜明个性的树,一棵暗里较劲的树,一棵与暗物质有同等威力的树。能够制造吸力,一棵树就等于一个黑洞。
“我喜欢的树/在杏林河畔/树叶,哗啦哗啦作诗/树汁,滴答滴答/滴入血液”,杏林喻指树的医者身份,这是一棵能够两手抓的树,随意就可例举一堆人的名子,郭沫若,鲁迅,大卫,还有村医梁文权等,他们左手写诗,右手开方,左右开弓,好不惬意。
“每当七夕来临/我就含住一根树枝/感受它的质感和膨胀”,七夕虽然不是年轻人的专利,但留有余香的手却鲜有松树皮,峡谷幽兰已见到第三代人,按北方人开玩笑的说法,她已走进“他奶奶的部落”,就是这样一个奶奶,让一棵树结满了温馨甜蜜的果实,每一个果壳都是一个想象的空间。
爱情的永恒在于它没有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年龄更不是爱情的高压线,读到这里我不知道是生活唤醒了树,还是树唤醒了生活,有时候,介入一点朦胧就会让一首诗即刻脱俗,峡谷幽兰做到了这一点。反复揣摩插入嘴里的树枝,它的质感,它的膨胀,不知不觉就会把读者引入只可意会的本能性的回忆里,而能够带来奇妙快感的诗歌,一定是有生命力的诗歌。
“ 我的树/土生土长/我的梦/正坐在枝上”,操着浓重河北地方口音的峡谷幽兰,没有将她的树弄成天上的神树,她的树就在身旁,接地气又土生土长。一棵树,有人想靠也无可非议,但诗人的梦却是坐在枝上,像骑马那样去驾驭一棵树的旅行。“诗人形单影只地写作……夜色潜入房中。再有一个简单音节就足以让世界欢呼雀跃,但是,那个夜晚已没有地方可以容纳一个词了。那时,诗人回到内心,寻找灵光一闪。”就让奥克塔维奥·帕斯的这段话,为《我喜欢的树》的延伸阅读做个结尾吧。
2017年1月2日
附《我喜欢的树》
文/峡谷幽兰
我喜欢的树,在光线下卷曲
在暗里,劲拔
或制造吸力
我喜欢的树,在杏林河畔
树叶,哗啦哗啦作诗
树汁,滴答滴答
滴入血液
每当七夕来临,我就含住一根树枝
感受它的质感和膨胀
我的树,土生土长
我的梦,正坐在枝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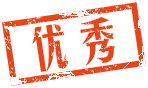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经典文学网
( 苏ICP备19050466号-1 )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经典文学网
( 苏ICP备19050466号-1 )